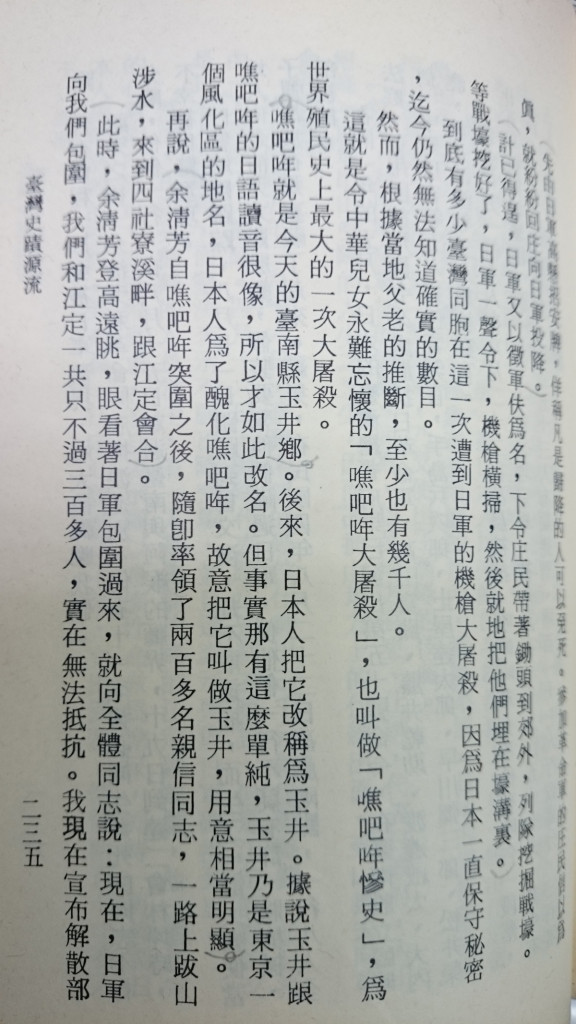最近看到楊渡在聯合報的一篇文章,談論的是湯德章。
該文指出,噍吧哖事件後,日本政府把噍吧哖改名為玉井,主要是因為玉井一詞是日本東京的風化區,故以此詛咒這個發起叛亂的地方。
楊渡想必是仇日仇過頭了,導致他連玉ノ井(たまのい)和玉井(たまい)都傻傻分不清。首先,日本政府把噍吧哖改成玉井,主要是因為玉井的發音tamai和噍吧哖tapani之故,壓根和日本的玉ノ井tamanoi完全無關。
第二,玉ノ井是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發展成風化區的。震災前,主要的風化區在淺早一帶。雖說玉ノ井在此之前也有幾間,但完全是非法營業,警察也會來玉ノ井取締這種私娼。但是大地震後,由於政府禁止淺草繼續發展私娼,大批業者才移往玉ノ井,此後逐漸發達起來。
噍吧哖改名是在哪一年?1920年。那時玉ノ井的風化產業一來不合法,二來應該不可能超越淺草,因此治台的日本政府斷不可預測玉ノ井將超越淺草成為風化區的代名詞,遑論用此來詛咒某個村子。
楊渡在文末說「寬容的心,慈悲的愛,才能化解這千古的恩怨」,問題是引用錯誤的資料,如何能化解恩怨?到底是誰內心仍存有國族的偏見呢?答案昭然若揭。
補充:
基於有人拿林衡道的《臺灣史跡源流》質疑本文,因此有必要在此詳述。
首先,玉ノ井本來就和「龜戶」齊名的私娼寮,本文也未否認此事。
爭議的點在於,1920年噍吧哖改為玉井是否真如林氏所稱,因日方憎恨此地之故。
本文也曾解釋,東京的銘酒屋營業地玉之井日語發音為たまのい;而台灣的玉井發音為たまい,兩者實屬不同。
另一需要說明的是,玉ノ井在分類上屬於私娼寮,與屬於公娼的遊廓不同。一般台灣人提到日本的風化區,不外乎就是吉原遊郭,因而對玉ノ井較無印象。另一方面也是因玉ノ井在1958年正式被日本政府禁止私娼,已成為歷史名詞。
東京市內的私娼發展,淺草十二階一帶要早於玉ノ井的。當時淺草地區有稱之為銘酒屋以及新聞縱覽所的私娼賣春店家。所謂銘酒屋,即是表面上賣酒,實際上從事私娼活動的飲料店;新聞縱覽所最初是提供民眾閱覽新聞雜誌之處,之後發展成暗中仲介私娼的據點。
根據1928年發行的《賣笑婦論考》一書,大正四年(1915年)東京市的銘酒屋數高達一千家,新聞縱覽所也有185家。這類私娼仲介場所,以淺草十二階 (凌雲閣)周邊為主要集中地。大正五年(1916年)警方展開私娼撲滅運動,迫使這類店家大幅減少。到了大正十一年(1922年),東京市內已無銘酒屋的存在。但是私娼並沒有因此消滅,反而以其他形式隱身於市井之中。由於難以取締殆盡,最終就以「待合」的方式(設有房間,客人在其中等待私娼)默認私娼的存在。
玉ノ井這個地方在明治維新後屬於「寺島村」,大正12年(1923年)才改為「寺島町」,當時屬於「東京市外」。這也是為何《賣笑婦論考》一書中引用的寺島町警察署資料是從大正12年末開始。我並無法找到大正12年以前的資料,但根據永井荷風的說法,大約在大正7年到大正8年之間(1918~1919年),淺草因開闢言問通り之故,有些銘酒屋便轉移到寺島村的玉ノ井。關東大地震後(1923年,大正十二年),淺草地區受災嚴重,私娼的發展遂大量轉移到玉ノ井以及龜戶這兩處。
問題就在於1920年,玉ノ井究竟是否出名到人人皆知,出名到重新命名噍吧哖的官員會故意使用玉井來詛咒噍吧年的居民。這方面的資料不好找,雖然這個網頁引用《賣笑婦論考》,指出大正8年玉の井僅有3戶私娼,到了大正9年則激增至95戶。但我無法在電子檔的《賣笑婦論考》找出此說法。
最後,我找到了這篇論文。作者引用小學館出版的《東京江戶年表》,該書提到大正十年左右「龜戶與玉の井開始出現私娼寮」。大正十年此一時間點確實符合整個脈絡。也就是淺草的私娼於明治末年快速發展,到了大正四年達到高峰。此後日本政府開始整頓,使得著名的淺草十二階的銘酒屋大量減少,但私娼則改以其他場所為營業點繼續存在。
此時,約在大正7年(1918年)有些銘酒屋轉移到東京市外的寺島村玉ノ井,促使該地私娼之發展。然而淺草的私娼並未消失,而是改以「待合茶室」的方式繼續營業。玉ノ井的銘酒屋有戲劇性的增長,得等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大地震使得淺草一帶遭到破壞,私娼們為了生活,大量移到隔壁寺島町玉ノ井。寺島町警察局的統計資料顯示,1923年六月末當時有352名私娼,1923年底因為9月的大震災而未進行調查。1924年6月末的私娼數為303名,人數減少可能是尚處於震災復興階段。但到了1924年12月末,人數增為359,已達震災前水準。1925年末更是增加到557人。
在網路上另還能找到一組數據。即昭和8年(1933年)時,玉ノ井的銘酒屋數量達497家,私娼數更達1000人。《賣笑婦論考》在探討東京內私娼盛行之處時,將龜戶列為第一,玉ノ井列為第二。可見在1928年的當時,龜戶與玉ノ井已是眾所周知的私娼地區。
昭和4年曾發行一本「全国花街めぐり」(松川二郎),該書介紹全日本特種行業地區,其中玉ノ井亦名列其中。而最令人饒富趣味的則是這個網站提到,昭和十年左右乃是玉ノ井私娼的高峰期,人數達2000-3000人,在當時可說是日本最大的私娼窟,而玉ノ井也成為私娼窟的代名詞。
更有趣的是這篇昭和五年的文章,內容提到大正十四年東京市內舉報最多賣淫之地,以淺草為首;郡部則是以龜戶、寺島(即玉ノ井所在地)為大宗,而龜戶遭到舉發的數量又遠大於玉ノ井。所以,若要羞辱噍吧哖,何不將此地改名為淺草阿、龜戶阿什麼的,幹嘛要改名為玉井?而且還少了一個の,只做半套。
由上面的資料可知,玉ノ井的私娼發展,最早雖可回溯到1918年左右,但規模應不大,知名度亦不如淺草。到了1920年左右,規模必然大於1918年,但仍不可能是全國知名。直到關東大地震後,玉ノ井因吸收原來在淺草附近謀生的私娼,規模才逐漸擴張,並且和另一個新興地龜戶齊名。《賣笑婦論考》成書於1928年,因此至少能推斷玉ノ井是在1925~1928年之間有著戲劇性的增長。但這也已是在台南玉井更名後五到八年的事情了。
進入昭和時代,玉ノ井快速發展,被列入「全国花街めぐり」,成為私娼寮的代名詞。玉ノ井之後雖毀於美軍的空襲,但戰後又逐漸興盛(雖然地點和戰前不同),直到1958年才被日本政府禁止。所以也許昭和時代的人對玉ノ井會比大正時代的人更有印象吧?
玉井其實也是日本的姓氏之一。若按照楊渡與林衡道的說法,不就暗示姓玉井的人通通都被詛咒了?同理,姓飛田的人也是祖先不知道幹了什麼事情被迫用這個名子嗎?
好了,論述結束,只差那本全台北市圖書館只有一本的青年日報版《台灣史蹟源流》還沒送來而已。
再補充:
終於拿到《台灣史蹟源流》了。
立刻翻到噍吧哖事件,果然發現網路上常常提到的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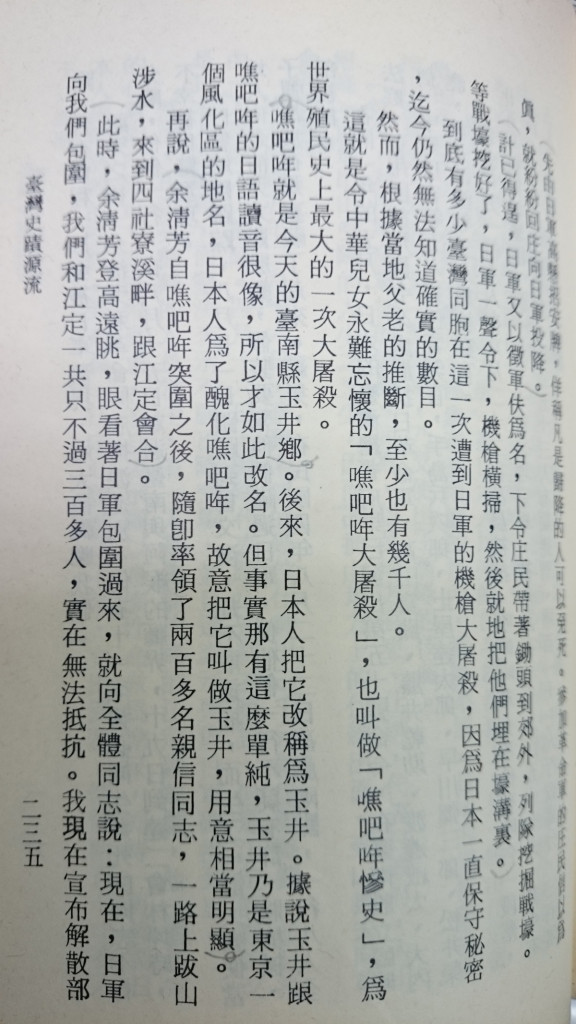 林衡道論噍吧哖改名為玉井的理由
林衡道論噍吧哖改名為玉井的理由
問題是,這種說法完全沒有資料佐證。
如前所述,玉ノ井是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才興盛起來。在1919年左右,只能算是萌芽期。第二,兩者的發音並不一樣。第三,日本也有其他地方稱為玉井,甚至有姓氏為玉井,難道這都是在羞辱人嗎?
如果是講日人統治台灣的政策,這都有史料可循,不特別引用倒是無妨,畢竟經得起檢驗。但是噍吧哖改為玉井一事,似乎沒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證是為了羞辱詛咒。這本書是林衡道口述的,沒有人知道他是基於何種資料做出此種結論。
林衡道生於1915年東京,此時為淺草十二階私娼最盛時期。我們以《賣笑婦論考》出版的1928年為界線,那年他13歲,也許多少耳聞玉ノ井的事蹟。1935年他二十歲,此使玉ノ井早已是聞名全日本的私娼寮。有沒有可能是他主觀地將台南玉井與東京的玉ノ井做連結,而得到日本人刻意「醜化」的結論呢?
日本埼玉縣與福島縣都曾有過「玉井村」,但為何在玉ノ井聞名全國之時,這兩個村都不出來抗議,要求改名呢?足見玉井對日人來說,就只是普通的地名而已。要說醜化、詛咒,證據可能都稍顯薄弱了。
追記:
楊渡最近寫了篇另一種凝視:楊渡》從芒果小村的民間記憶說起,內文說他找到直接證據證明日本人命名玉井是意圖羞辱台灣人。
他說:「但台灣仍有親日者為日本開脫,說玉井命名不是如此,只是因為噍吧哖其聲近乎日語玉井,故名。但他們只是推論,無法證明,而我卻有當事人後代的證言,故有說服力。」
哇,竟然有當事人的後代可以證明日本人用玉井是為了羞辱台灣人,真是可惜可賀,這可說是學術界的大發現阿~我們趕快來看看這所謂的證據是什麼。
演講後,一位聽講的玉井老先生私下找我談話。他說,小時候聽祖父談及,那時日本槍殺砍頭都有。砍頭後,身首分離,頭滾落到山谷裡去,身體撲倒在地,屍橫遍野。日殖政府不許收屍,放任腐爛,整個山谷充滿屍臭,無人敢靠近,唯有野狗徘徊。數日後日人才允許收屍,可是面目多已腐爛,根本無法辨識。唯一可辨認者,只剩下未腐爛的衣服,親人或許還可認得的,便收去安葬。雖然無頭,亦毫無辦法。而所有留存的頭部或屍體,就一起埋葬,成為萬人塚。後來有人燒香,乃成萬姓爺廟。
嗯?證據呢?證據呢?證據呢?玉井阿伯說了一堆日軍殘忍無道的事跡,可是這跟玉井命名有什麼干係嗎??
這就是所謂當事人後代的證言?我也是醉了,到底證言了什麼??
算了,人家要精神勝利法,我們也干涉不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