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了解愛因斯坦與原子彈製造的關係,那麼本片可能無法滿足,因為本片的英文標題雖為”Einstein and the bomb”,但內容卻非專注在原子彈的製造上。但好在中文標題多了「愛因斯坦的自白回憶錄」,或許能讓你做好心理準備,在觀看時能夠理解這部片主要呈現愛因斯坦的內心獨白。
愛因斯坦畢竟是世界偉人,若要深究其事蹟,不太可能用一部紀錄片就能闡述。因此,本片的主要時間範圍落在愛因斯坦踏上英國與定居美國之間。而探討的主題,無疑就是愛因斯坦與原子彈。只不過,切入點是他對原子彈的態度,不是製造,畢竟他也真的沒有像奧本海默那樣深度涉入。
但若要談到愛因斯坦對原子彈的想法,又不得不提到納粹德國。因此,《天才與原子彈:愛因斯坦的自白回憶錄》使用不少歷史影像,加強納粹對猶太人迫害的印象;而正是有了這些印象後,對於愛因斯坦那句「如果我知道德國人不會成功製造原子彈,我不會做任何事情」才會有更深的體會。
呈現方式
本片不太算是傳統的傳記片,而是用戲劇搭配歷史影像、特效片段去呈現那些愛因斯坦留下的自白,並將敘事導向對原子彈的悔意。
但不得不說,《天才與原子彈:愛因斯坦的自白回憶錄》前半部的的節奏有點平淡,加上一些頗帶詩意的處理方式、聽起來很平淡無味的和平堅持,曾讓我考慮放棄。好在後半段主題浮現,才有個焦點能夠吸引我看下去。
可是,戲劇的部分表現得不太合我胃口。我能看到愛因斯坦那種憂鬱與哀傷的表現,但因為在前半部無法帶入情緒,使得他的那些自白感覺很無病呻吟。而且他的英國朋友蘭普森(Locker-Lampson)也整天面露苦色,看著看著就不覺興心情為之低落,索然無味。印象最深的是,女保鑣的其中一名(Barbara Goodall,後來與Lampson結婚),以驚恐的神色展現質能轉換的可怖。可是,對於非科學界的人來說,愛因斯坦講的那些,應該是很抽象又難懂的,她的反應實在讓人出戲。
原因或許是Goodall的驚訝與我並無共鳴。我當然知道原子彈的威力,但對我來說它是結束戰爭的重要工具,減少美軍可能的登陸作戰的傷亡。但對Goodall來說,當時確實很難想像原子彈帶來的毀滅能力。基於此,若不以戲劇呈現,改用一般的重演,也許就不會突兀。但這樣做,可能會使本片變得扁平,少了人物的立體感。尤其是強調「自白」時,僅依靠旁白念過去,觀眾的印象就不深刻了。
原勝與《改造》雜誌
《天才與原子彈:愛因斯坦的自白回憶錄》片尾進入最重要的主題:愛因斯坦對於原子彈究竟持有什麼看法。節目至今為止的敘述,愛因斯坦未曾直接參與曼哈頓計畫,但他的理論卻間接促成原子彈;而且,當傳出納粹開始研究原子彈時,愛因斯坦寫了封信給羅斯福,呼籲美國也該進行研究。
原子彈問世了,但沒有用在德國,反而投在日本。即便愛因斯坦本人沒有責任,但他仍對此抱有內疚。而當愛因斯坦晚年時,一位名叫原勝(Hara Katsu)的日本記者寫信質問愛因斯坦,為何明知原子彈的威力卻仍參與計畫。
本片的表現方法是,讓飾演日本記者的演員直接進入愛因斯坦的房間,展開辯論。但事實上,原勝與愛因斯坦僅通過信,未曾謀面。紀錄片並未介紹原勝,我上網Google後,發現一篇日文閱讀心得,講的是1977年出版的《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の平和書簡3》(愛因斯坦的和平書信3),剛好提及這段往事。
原勝是當時《改造》雜誌的編輯長,這本雜誌創刊於1919年,曾於1922年邀愛因斯坦訪日。1944年一度因日本軍部壓力解散,但於1946年復刊。愛因斯坦與當時接待他的日方人員仍有聯繫,因此當GHQ解除原子彈資訊管制後,原勝於1952年9月15日寫信質問愛因斯坦上述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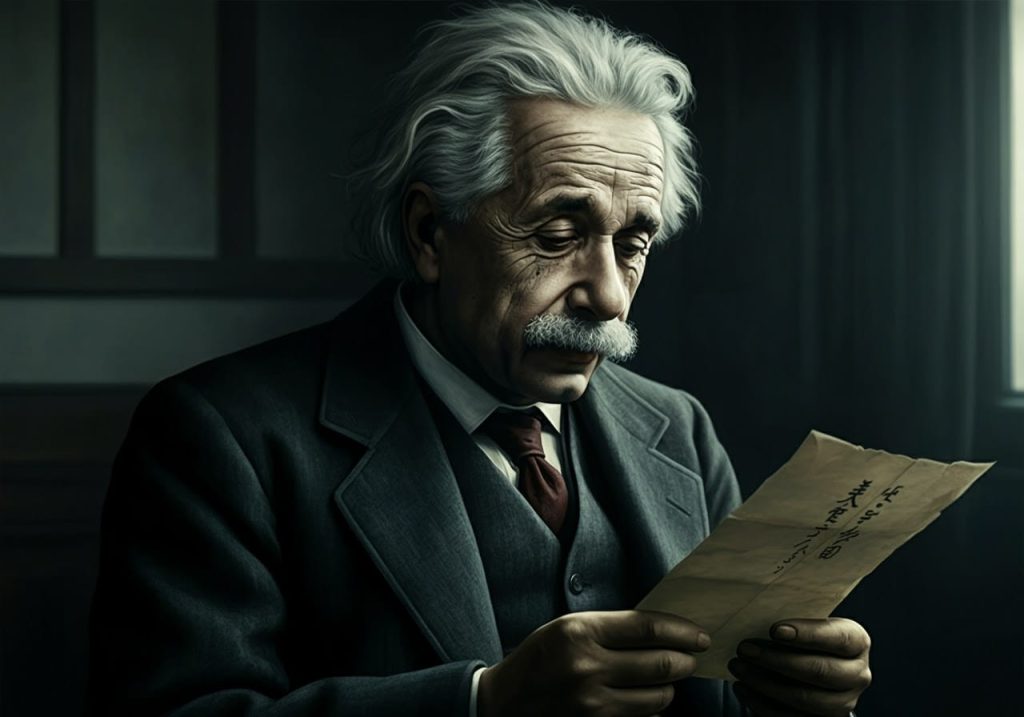
愛因斯坦的答案,與《天才與原子彈:愛因斯坦的自白回憶錄》片中相同,強調除了提出理論外,他只有寫過一封建議進行原子彈實驗的信給羅斯福總統;且考慮到當時德國的情勢,除了比他們更早完成原子彈之外,難有他法。
《改造》雜誌光聽名稱就很左,而其確實也關注於社會主義與勞動議題。擔任翻譯的篠原正瑛不滿此答覆,隔年再度去信質疑,愛因斯坦建議羅斯福發展原子彈,是為了想報復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愛因斯坦回信表示,自己並不是無條件和平主義者,當有敵人威脅要奪取自己或家人生命時,他支持使用暴力。
《改造》當然不會就此收手,篠原再度發信責問,以事實來論,愛因斯坦應該能接受對廣島與長崎使用原子彈吧?這次愛因斯坦明確表達了他的立場:
「任何情況下我都反對暴力。但若敵人意圖以抹殺生命作為其目的,則屬例外。我始終認為,對日本使用原子彈是有罪的。但是,我幾乎無法阻止這個宿命的決定,能做的很少,就如同您對日本人在朝鮮與中國的行為,能夠負責的程度一樣少。我不曾主張對德國使用原子彈那種事情是正確的,但我相信,必須無條件地阻止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單獨擁有這種武器。」(684-685頁)
這立場呼應本片提及的那句話:「Had I known that the Germans would not succeed in producing an atomic bomb, I would have never lifted a finger.」但是誰又能預測未來呢?以當時希特勒如日中天的聲勢,愛因斯坦不可能預測德國終將失敗,那麼他自然會建議羅斯福進行研究。《改造》雜誌那群人如此逼問愛因斯坦,在我看來並無意義;況且他們為什麼不去找奧本海默呢?
可能的原因是,以1950年的資訊來看,非英語圈的人並不熟知奧本海默。加上愛因斯坦曾經訪日,又具備和平主義者形象,才會讓《改造》雜誌將矛頭指向他吧?